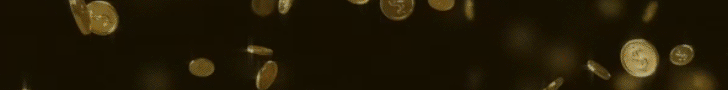維克作為作家、音樂家和藝術家閃耀光芒。
李羅伊傑森
作為一名說唱歌手,Vic Mensa 繼續為我們這個時代一些最重要的曲目做出貢獻,隨著他的影響力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迴響,他將做得如此出色直到永恆。 他曾與 The Internet、Chance the Rapper、Snoh Aalegra、BJ The Chicago Kid、KAYTRANADA、Juicy J、Flume、Joey Purp、Asher Roth 和 Chief Keef 合作。 他與其中許多人的合作將為人們播放,只要他們能聽到我們和我們時代的歌曲。
與當代詩人的文學聯繫根深蒂固,就像河流可以雕刻砂岩一樣。 他 在早餐俱樂部引用多產詩人和哲學家貝爾胡克斯的話,節目流行偶像,宣布未來的總統候選人, 福布斯 30 歲以下 30 歲的應徵者,以及 喜劇演員 日威 被稱為“最具標誌性的黑人廣播電台”。 他是一位出版作家 滾石.
他交付了 乾淨的水 系統,狂歡節,和 Dave Chappelle的 到加納。 後兩個是給他的 黑星線節. 作為一名活動家,他的個性和同情心以及 使我們所有人變得更好的人類核心 在質疑之下顯而易見。
維克——在一次成功的表演之後,在一次成功的旅行和一次良性的冒險中——睡著了。 和生活一樣,睡眠讓位於做夢。
在這個故事中,訪談混合了離奇的幻想和超飽和的主題,在文學的氣質沙中。
維克在夢中遇到了低地鄉下的一個低落男人。
他自我介紹為 Fingal O'Flahertie,一頭烏黑的頭髮蓬亂而濃密,中分。 在 Vic 的夢裡,O'Flahertie 的頭髮像紳士一樣光滑地貼在他的頭皮上,記憶猶新,彷彿楓樹的蒸汽或一群法國蚊子在他的頭上盤旋。 Fingal O'Flahertie 曾經是 成為的人. 迷路了,兩人在當時破舊的夢中找到了彼此。
Fingal 穿著一件毛皮襯裡的外套,破爛不堪,底部像粉紅色霓虹燈一樣燃燒。 他的整個角色都沾上了顏料,粉色、綠色和灰色。 他的手是他身上唯一沒有生命的部分。 他的其餘部分都在快死的馬車上,沒有什麼比這更鮮活了。 不過,他的角質層、指關節和手掌交界處的皮膚像棕褐色珍珠一樣閃閃發光——天使般的、完美的、安定的。
芬戈爾被流放,留給世界的時間不多了。 他說,在悲傷變得清晰之前。 “我有一個好久不見的姐姐,”他說。 “我期待再次被藍色中國和劇院包圍。 監獄使人的心結成石頭,使記憶、財務和人際關係成為笑柄。”
“你坐過牢嗎?” 維克問。
芬加爾說:“刑未盡,雖放之。”
在他的沉默中,他明確表示他無話可說。 然後,維克傾訴了真相,因為他的夢想是用誠實縫合的,就像清醒的生活是用時間縫合的方式一樣。
“當我在監獄裡的時候,”維克說。 “我在冥想。 我身體上在牢房裡,但精神上——我離監禁還很遠。 我是,我他媽的很自由。”
“而不是從不確定性或許多嚇壞了 原因 這種情況,”維克說,“我立即接受了。 我開始感謝上帝的祝福。 我,我的整個事情是——我感謝上帝以任何形式的祝福。 而且我一直專注於冥想,以至於我沒有壓力。”
“對於幼鴿來說,所有的飛行都會找到新的高度。 老鳥不聞風,祈願乘光飛翔,”芬格爾說。
“不,我只是每天都告訴自己,我不再沉迷於我應該在的地方或事情應該的樣子,”維克說。 “我接受現在的情況。 因此,我對此感到很興奮,因為我擁有我熱愛的東西,我很高興能與全世界分享。”
“我在音樂行業或作為一名活躍的創作者的時間一直專注於樂趣,但我意識到樂趣和快樂並不是同義詞,”Vic 說。 “我一生真正渴望的是快樂。 我為樂趣而做的許多事情實際上與我生活中保持快樂的方式背道而馳。 我正在為快樂而放棄樂趣。”
Fingal O'Flahertie 說:“每個人都會殺死他所愛的東西。 有些人用苦澀的表情來做,有些人用奉承的話來做。 懦夫用吻,勇者用劍。”
兩人穿過法國,遠離沉悶的法國,流亡和世紀之交的法國。 隨著夢想中的法國的成長,棕褐色色彩斑斕。 直到 France 在他們腳下嘆息,Vic 也睡了。 很長一段時間,什麼都沒有閃耀。 葡萄園荒廢多年。 鄉間小路上滿是低沉刺骨的寒風。
他說:“有的人年輕時扼殺愛情,有的人年老時扼殺愛情; 有些人用慾望之手扼殺,有些人用黃金之手。 最仁慈的人會用刀,因為死人很快就會變冷。”
維克花了一些時間才平靜下來,思考著如何回答。 然後他說,“大約一年半前,我正在製作 Kanye 專輯,我想 唐達 一。”
“Kanye 正在芝加哥舉辦聆聽活動。 之後我要去參加派對。 之後我要去參加一個 Juke 派對; 它在芝加哥被稱為 Juke,”Vic 說。 “這就像步法音樂,但也像高中派對一樣天真無邪。 基本上是在磨。”
“派對和夜晚開始了。 有人把一大塊莫莉放在我手裡。 我拿走了莫莉的大塊,”維克說。 “我參加 Kanye 活動的整個過程中,我可能喝了一整瓶亨尼酒。 我太變態了,當我參加派對時,每個人都已經開始搖擺不定了。 而且我真的喝得太醉了,無法做出任何正確的決定。”
“我剛剛開始一段新的關係,就是我現在的關係,”維克說。 “我發現自己酒後駕駛這輛路虎攬勝在湖濱大道上超速行駛,試圖為我的女朋友做一些不尊重的事情道歉。”
“然後我就跑出了馬路——總計這輛價值 120,000 美元的車,後座上有一把臟手槍,”維克說。
維克說:“我們關注的焦點和我們的精力都變成了現實,一直到電子之下。 它是非物質的; 它是特別的。 它是能量。”
“在那之前的一周,或者幾天之前,我有生以來第一次來到清真寺。 我在祈禱; 當時我經歷了很多,”維克說。 “曾經是我朋友的某個人想殺了我,因為我大聲疾呼,因為他偷了我的東西,因為我和我本不應該捲入的人一起被困住了。”
“所以,有人想殺我。 我的錢都花光了。 在情感上,我很崩潰,”維克說。 “我在祈禱,我在祈禱我在向上帝祈禱。 這是我第一次認真地來到神的殿中。”
“感謝上帝的恩典,我的朋友及時趕來,把槍從現場移走,把車修好了,我不用為這個狗屎付出代價。” 我不必坐牢,因為我已經有兩項持槍指控,”維克說。 “就好像我無法解釋這個。 那是我無法解釋為什麼我真的是個好人的事情。 我的祈禱得到了回應。 我什至還沒有意識到我在祈禱什麼。”
Fingal O'Flahertie 說:“無論是乳白色的玫瑰還是紅色的玫瑰都不會在監獄的空氣中綻放。”
維克說:“我已經戒酒一年半了。 我只是刪掉了很多東西。 我和我的治療師一起瀏覽了所有我最喜歡的歌曲,並意識到其中的大多數,我讓他們清醒了。”
Fingal O'Flahertie 說:“世上沒有什麼是無意義的,而痛苦是最不重要的。 隱藏在我本性中的東西,就像田野裡的寶藏,就是謙遜。 這是我最後留下的東西,也是最好的東西。”
Fingal 問 Vic 資本主義如何影響工藝。 “積極消極,”維克說。 “我認為資本主義與我們創造的幾乎所有存在於我們美國參照範圍內的東西絕對是不可分割的——無論你是否贊同它,你是否反對它,或者兩者兼而有之,就像我想說的,大多數我們中的人可能是。”
“從根本上說,我在意識形態上反對資本主義,因為資本主義與奴隸制和白人至上密不可分,並且是這些意識形態和控制形式無處不在傳播的主要動機,”維克說。 “我是非洲人,所以我一直是資本主義的受害者。”
“現在就我們在音樂行業製作的音樂而言,在說唱遊戲中。 說唱是如此資本主義,就歌詞而言,”維克說。 “我和一個朋友談過這件事。 這位朋友出生在聯邦,一生都在監獄裡進進出出。 他是一個活躍的幫派成員、毒販、殺人犯,九個人——也是一個非常好的人。”
“我愛他。 這就是他一生的處境。 當你出生在聯邦監獄時,你的選擇可不是最該死的,你知道嗎?” 維克問。 “人是環境的產物。 在某種程度上,我們正在談論資本主義,伙計,因為他告訴我,他就像, 芬太尼是有史以來最好的 sh**. 我就像, 你他媽的聽到自己了嗎?“
“對於男人來說 嚴酷的正義如約而至 並且不會轉向一邊,”芬戈爾說。 “它殺死弱者。 它殺死強者; 它有致命的步伐。 它用鐵治愈它殺死強者,可怕的弒父者!”
“Fingal O'Flahertie 向正義吐口水,”Fingal O'Flahertie 幽默地說,也許還有一點失火。 他也吐了。 維克認為他看到紫色的閃電在他們前進的路上在遠處微笑。
“芬太尼正在謀殺這麼多人,”維克說。 “有這種平衡,惡魔們不想在沒有芬太尼的情況下削減毒品,因為它不會達到同樣的效果。 毒販喜歡芬太尼,因為它讓他們能夠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濫用毒品。”
“我們已經在貪婪地交易,但也有過度的細線。 你越過了那條線,現在你殺死了所有接觸到你的狗屎的人,”維克說。 “他說, 嘿,這些人有一個選擇,伙計. 他們選擇吸毒. 我想,但如果你選擇服用 Xanax 來緩解你的焦慮,而且它是用芬太尼減量的,那不是一個選擇。”
“他表達了一種深刻的資本主義心態。 那是對人的利潤,”維克說。 “資本高於一切。 這與你在幾乎每一首說唱歌曲中聽到的情緒都是一樣的。”
“最基本的說唱口號是 比特幣的錢. 在基本層面上,這就是說美元鈔票比女性更重要,”維克說。 “文字有如此大的力量。 你是說金錢比生命之源更重要。”
“我們訂閱的同一件事要為我們的毀滅負責,”維克說。 “我們是黑人。 我們一直是,我們仍然是資本主義的受害者,不管我們有沒有 Jay-Z、Tyler Perry 和 LeBron James。 無論我們是否有一些傑出的黑人人物和奧普拉溫弗瑞突破並成為億萬富翁,你都有 1 美元或 0 美元的財富 在普通黑人家庭中,與普通白人家庭的一百個相比。 我們仍然是資本主義的受害者。”
“非洲的資源仍然是由南非、英國、荷蘭和葡萄牙的公司開采的——仍然是我們的黃金、我們的鑽石。 資本主義正在扼殺我們,但我們仍然訂閱,”維克說。
“英國舞台不允許出現聖經人物,”O'Flahertie 小聲說。
“我從未見過我的祖父——他的官方宗教是最初的伏都教,它通過中間通道被運送到路易斯安那州,成為現在眾所周知的伏都教,”維克說。 “我剛剛接到了這個電話。 你懂。 多年來我一直感受到這種呼喚。 這就像從天而降的能量告訴我,你這一生在地球上處理的很多事情都不是你的。 回家; 我們能幫你。”
“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催化劑,讓我開始在加納度過很多時光,”維克說。 “我總是偶然發現 Mami Wata——巫毒教的水之女神。”
“我與一位作家 Mami Wata 女祭司取得了聯繫。 雖然邊境關閉了,所以我偷偷穿過加納,進入多哥,進入貝寧,然後騎著摩托車偷偷通過一個邊境檢查站。 然後是另一個。 我繞過一個大垃圾場,穿過一片海灘,然後上了車,又回到了過去。”
“這絕對讓我覺得所有這些武斷的界線都是在相同種族背景的人之間劃定的。 我在加納的經理說母語,這與多哥和貝寧的語言相同。 這是一些胡說八道**,”維克說。
法國早已從他們的腳下消失了。 棕褐色讓位於同性戀自然界最偉大的色調。 生物和發光多樣性的書籍在他們的腳下歌唱,風解除了他們行走的輕負擔。
“從加利福尼亞到墨西哥,從德克薩斯到墨西哥,”維克說,“那個 sh** 就是墨西哥,伙計。 而你們這些 ni***s 只是在上面設置了邊界,並試圖將人們拒之門外。 沒有意義。 沒有任何意義。 我不同意這裡的明顯命運。 我在任何地方都不同意明顯的命運。”
他醒來時還沒有和 Fingal O'Flahertie 說再見,他在一個更好的地方。
你可以在 Instagram 上關注 Vic 点击這裡, 在推特上 点击這裡,並訪問他的商品、音樂和音樂視頻 点击這裡.
來源:https://www.forbes.com/sites/rileyvansteward/2023/01/23/vic-mensa-poet-and-musician-dreams-of-wild-pe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