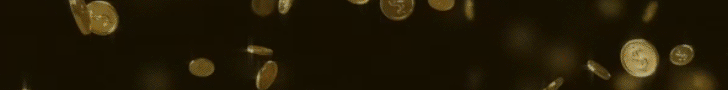在忽視所有其他問題的同時解決地球和人類的福祉是不可接受的 …[+]
法新社通過蓋蒂圖片社
我們今天所知道的環保運動比擁抱樹木和撿垃圾要大得多。 Dakota Access Pipeline 和密歇根州弗林特的含鉛水等重大危機已引起全國關注資本主義濫用環境的方式不僅損害了土地本身,而且損害了水等重要的自然資源——反過來,弱勢群體如何喜歡美國原住民和美國黑人面臨最嚴重的影響——這是由於 環境種族主義.
當談到地球及其居民的生存時,我們一直在朝著“漲潮托起所有船隻”的方向前進——健康的土地、水和植被很重要,不僅是為了美麗的風景,而且是為了每個以某種方式依賴自然世界的人(我們所有人)的福祉。 然而,有一個原因仍然明顯地被排除在這些談話之外:動物福利。
如今,許多激進主義運動規模龐大且相互關聯——社區組織和學者提出了一些想法,例如 交叉性,在 1980 年代由批評種族的學者 Kimberlé Crenshaw 首次創造。 交叉性是一個分析框架,它考慮了交叉身份(例如種族和性別)的獨特影響,而不是一次只探索種族主義或性別歧視等單一現象。 超體性 是另一個重要的想法,由人文學者 Stacey Alaimo 在 2010 年代初期提出。 它指的是承認人類、其他動物和自然世界其他方面之間的相互聯繫。 這些想法幫助公眾擴展了我們構想環境問題和解決方案的方式。 但我們似乎無法擺脫的一個幽靈是物種歧視——認為人類優於所有其他動物並因此特別有權受到道德考慮的假設。
誠然,環保主義在美國文化中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 從 19 世紀瓦爾登湖式的浪漫主義和泰迪·羅斯福的十字軍東征到 保護 這個國家的自然美景,直到 20 世紀,問題的癥結在於保護(不管你信不信,這是一個 兩黨 導致很長一段時間)。 社會對環境的關注主要與其實際物理狀態有關——例如森林砍伐、水壩、它們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以及為了自然而欣賞自然等問題。 到了激進的 1960 年代,隨著雷切爾·卡森 (Rachel Carson) 等人的聲音引起公眾對 相互關係 在生態和人類健康之間。 風險突然變得比保護我們喜歡看的地方更高——很明顯,對環境的傷害意味著對生活在其中的人的傷害,這包括人,無論我們多麼認為現代社會與自然界。
在過去的 50 年裡,環保主義者的批評變得多管齊下,考慮到相互關聯的種族問題, 勞動,以及後期的許多失敗 資本主義. 貧困人口和代表性不足的種族群體將面臨氣候變化的最嚴重影響,例如自然災害。 只看去年的 颶風季節 以美國為例。 本·查維斯創造了“環境種族主義”一詞 40年前,在有毒農場廢物污染北卡羅來納州沃倫縣一個貧窮黑人社區土壤的背景下。 從那時起,這個詞就被應用於一系列其他問題,在這些問題中,有色人種是環境污染的主要受害者,通常是在強大的公司手中。 在 Google 上快速搜索一下,您會發現在美國及其他地區不乏示例。 當我們聽到“環保主義”這個詞時,像查維斯和卡森這樣的領袖和知識分子極大地拓寬了我們的思維範圍。
儘管這種交叉方法越來越多,但動物權利仍然被視為邊緣問題,而且通常被視為不嚴重的問題。 學者和活動家批評化石燃料公司,但許多相同的聲音無話可說 工廠化農場. 當工廠化農場確實惹人生氣時,談話的焦點往往是排放、水污染、土地使用和勞動條件。 那些是 所有關鍵問題,但在我看來,這些對話往往會四處亂舞 動物的痛苦 構成這些行業和實踐的核心。
這裡有一個恰當的例子:“這改變了一切”一書的作者娜奧米·克萊因 (Naomi Klein) 擁有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這些作品出色地審視了環境與社會問題(如性別歧視和貧困)之間的交叉點。 然而,據她自己承認,她對將這種分析擴展到非人類動物不感興趣,她說:“我參加過的氣候集會多得數不清,但北極熊呢? 他們仍然不為我做這件事。 我希望他們一切順利,但如果我學到了一件事,那就是阻止氣候變化並不是真正關乎他們,而是關乎我們。” 作為記者 科里·晨星 說起來,這是“人類中心主義冒充環保主義”。 以環保主義的名義虐待動物的其他例子浮現在腦海中,例如組織製作 比賽 出於殺死入侵物種以及動物園和水族館將動物留在 囚禁 為了所謂的“保護“
進步的、具有前瞻性思維的環保主義者已經展示了考慮種族、性別和性取向等社會類別與環境問題交叉的方式的能力——但他們往往只是在考慮物種歧視之前停下來。 這是包容性的失敗,而且是危險的短視行為。
現在是我們開始在這個框架中看到個體非人類動物的福祉的時候了。 一方面,承認非人類動物的內在價值不僅僅是多愁善感或多餘的,這只是一個公平問題。 我們承認人類個體本身就很重要,一個正常運轉的社會會最大限度地減少其成員的痛苦。 我們承認生物多樣性具有內在價值,不僅僅是因為瀕臨滅絕的動植物物種可能影響人類社會的方式,而是因為它們有權在沒有不可避免的痛苦的情況下生存的簡單美德。 這是對生命的基本尊重,沒有任何理由不應該延伸到非人類動物身上。
但是,如果對生命的尊重不足以成為認真對待動物的充分理由,讓我們承認傷害不僅會發生在土地與人類之間,也會發生在人類與非人類動物之間——即使是在個體層面。 我們在人畜共患疾病的案例中看到了這一點:研究人員已經確定了一些 疾病, 從絛蟲到肉毒桿菌中毒,它們有通過狩獵和食用野生動物傳播給人類的風險。 這些疾病有可能直接或間接影響人類(例如生態系統破壞造成的經濟壓力)。 有些甚至有可能發展成全面的大流行級別的爆發。
誠然,這並不是因為惡意甚至冷漠而將動物福利排除在這些對話之外。 不幸的事實是,要在所有這些其他方面做出積極的改變已經夠困難的了——工人權利、種族正義、土著土地權利,更不用說氣候變化的全方位威脅和化石燃料工業造成的廣泛環境退化. 很容易看出有多少人——甚至是堅定的環保主義者——會因為所有這些其他緊迫問題而忽視動物痛苦問題。 但正如交叉的、關注環境的當代組織者和學者告訴我們的那樣,宣傳不需要非此即彼。 我們有空間同時關心這兩個問題,在某些情況下,這兩個問題根本不是孤立的。 事實上,人類和非人類動物的命運交織在一起的方式不止一種——我們不妨開始這樣做。
來源:https://www.forbes.com/sites/briankateman/2023/02/01/the-environmental-movement-forgot-about-anima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