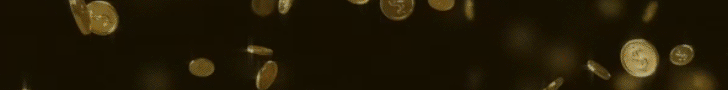(攝影:Mikhail KLIMENTYEV / SPUTNIK / AFP)(攝影:MIKHAIL KLIMENTYEV/SPUTNIK/AFP via Getty …[+]
通過Getty Images的SPUTNIK / AFP
當我們目睹烏克蘭發生的恐怖事件時,我們無法理解俄羅斯人民對以他們的名義所做的事情無動於衷。 到這個時候,俄羅斯聯邦各地應該會明顯地發出大規模的恥辱或憤怒的抗議,其規模至少足以遏制克里姆林宮的政策。 毫無疑問,警察國家的鐵腕手段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這種平靜:抗議者的廣泛逮捕、多年來通過公開暗殺持不同政見者來散佈恐懼、無情的宣傳等都取得了預期的效果。 但是,問問任何一組專家,他們都會告訴你問題更深層次,實際上深入俄羅斯公眾的心靈。 目前尚不清楚普京的個人聲望是否受到了巨大打擊。 相對受人尊敬的列瓦達民意調查機構認為他的支持率仍高於 80%。 最近對逃往國外的人數的估計徘徊在 700,000 左右,與總人口相比微不足道。 僅僅是俄羅斯人根本沒有獲得可以改變他們思想的信息,還是他們居住在這樣一個平行宇宙中以至於他們免疫?
自冷戰後期以來,時代確實發生了變化,當時在鐵幕背後,來自西方的消息被認為比克里姆林宮的消息更寶貴、更可靠(也更理智); BBC 俄語部和自由歐洲電台等消息來源被尊為真理之源。 耶魯大學資深俄羅斯問題專家托馬斯·格雷厄姆 (Thomas Graham) 教授表示,蘇聯公民“即使是他們自己的本地新聞也無法相信官方媒體——切爾諾貝利只是一個例子——所以他們學會了相信我們的替代品。” 但這不僅僅是硬新聞。 西方充滿了娛樂、魅力、時尚、體育和搖滾音樂,與克里姆林宮單調乏味的廣播形成鮮明對比。 蘇聯人在軟實力鬥爭中同樣慘敗,反信息通過軟實力被動而有效地流動。
但那是那時。 在普京的領導下,俄羅斯媒體做出了持續而成功的努力來提高自己的水平,增加電視頻道,增加年輕和性感的面孔,按照世界標準美化製作價值,特許經營西方節目,模仿他人,創造了一個令人眼花繚亂、自給自足的生態系統——可能不受外界滲透。 然後是互聯網世界。 大多數觀察家認為,俄羅斯的在線信息空間並不像中國那樣絕對封閉。 更深層次的問題似乎是,俄羅斯人本身對西方媒體和信息並不那麼開放,不覺得有必要,實際上與任何形式的道德自我意識隔絕,部分原因是莫斯科對其媒體景觀進行了現代化改造,而且它的宣傳生態系統,非常狡猾。 彼得·波莫蘭采夫 (Peter Pomerantsev) 2014 年關於該主題的著名著作《沒有什麼是真實的,但一切皆有可能》(Nothing Is True But Everything Is Possible) 概述了俄羅斯電視如何發展出一種宣傳形式,這種形式並沒有完全提供他們的真實版本,而是通過浮動來攻擊真實的概念關於任何與克里姆林宮有關的事情的多重——通常是相互矛盾的——陰謀論。
臭名昭著的 2014 年 17 月,荷蘭飛往馬來西亞的民用航班 MHXNUMX 被擊落就是一個完美的例子,這顯然是由在烏克蘭境內運行的俄羅斯導彈系統造成的。 莫斯科媒體聲稱有證據表明它被一架烏克蘭噴氣式飛機擊落,然後被烏克蘭防空系統擊落,這是一次載有屍體和其他許多東西的自殺式飛行。 幾年後,海牙國際法院不可否認地正式將責任歸咎於克里姆林宮控制的分離主義勢力,此時俄羅斯公眾已經失去了所有興趣。 這種密集的虛假信息攻擊的長期結果是當今民眾普遍存在的憤世嫉俗和冷漠態度:每個人都在撒謊,沒人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為了理智,把一切都留給掌權的強人。 這實際上轉化為一種對克里姆林宮令人髮指的行為的道德關閉開關,尤其是在國外。
莫斯科從未面對過它的殖民歷史(圖片來源應閱讀 MLADEN ANTONOV/AFP via Getty …[+]
法新社通過蓋蒂圖片社
部分責任在於西方。 在普京時代,隨著克里姆林宮媒體機器的趕上,我們顯然把目光從球上移開,在某種程度上相信歐美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信息不言而喻,不需要額外的宣傳。 曾經在俄羅斯非常有效的西方傳統媒體仍然採用簡單地“說實話”的過時方法,提供客觀新聞並強調新聞,這對莫斯科複雜的虛假信息技術與娛樂相結合幾乎沒有影響。 那也是從 2001 年開始的“反恐戰爭”年代,當時自由世界的注意力轉移到了別處。 也是俄羅斯公民可以基本上暢通無阻地出國旅行,並在更自由的環境中親眼目睹民主進程混亂內部的時代。 對於許多人來說,這讓他們想起了葉利欽時代的混亂狀況以及隨之而來的社會經濟困難、內戰、無家可歸的頭巾等。
“他們開始相信,西方在意識形態上沒有什麼可以教給他們的,這與克里姆林宮的信息非常一致,”保衛民主基金會著名的普京批評家伊万娜·斯特拉德納 (Ivana Stradner) 說。 “他們喜歡西方的生活方式,但不喜歡它的價值觀。 石油資金源源不斷湧入。幾十年來,他們第一次買得起消費品和奢侈品。 克里姆林宮說服他們,俄羅斯的例外主義和愛國主義,實際上是至高無上的,與穩定和成功共生。” 最關鍵的是,它允許絕大多數政治上惰性的人保持這種狀態。 最終,莫斯科有勇氣在軍事和信息方面從防禦轉為進攻,並確信自己已經完全保衛了自己的主場。 畢竟,針對西方,直到今天,同樣的技術已經造成了一種兩極分化的憤世嫉俗,對共識信息或“客觀”新聞具有腐蝕性的不信任。 無法彌合我們自己社會內部的鴻溝,我們已經失去了彌合俄羅斯心靈和思想鴻溝的能力。
可以說,在烏克蘭全面入侵之前,俄羅斯公眾並不覺得有必要了解政府希望他們了解的更多信息。 持不同政見者的謀殺、國內外的投毒和開窗事件、對格魯吉亞、頓巴斯和克里米亞的軍事入侵,都沒有動搖公眾的舒適區,足以引起克里姆林宮的警覺。 但從基輔襲擊失敗開始的烏克蘭災難已經改變了一切,根據格雷厄姆教授的說法,“造成了人們多年來似乎第一次真正關心的信息短缺。”
關於戰區挫折的可靠消息,突然需要動員應徵入伍者,他們訓練有素並被派往被毆打以及製裁(在各省)日益增長的經濟影響,為西方的反信息提供了機會冷戰期間存在的那種——甚至在老一代中也有一點,據所有人說,他們大多被認為是遙不可及的。 他們是第一個被後蘇聯多頻道有線電視的偉大擴張所包圍的人,對於那些習慣了以前廣播條件的人來說,如此令人愉悅和包羅萬象,長期以來一直是國家失敗的陰鬱象徵。 克里姆林宮對這種日益增長的溫室效應非常有信心,以至於多年來,反對派報紙在普京的領導下被允許存在,因為他知道與所有渠道相比,它們的影響力是多麼小,在各種寡頭統治下普遍由國家控制。
不過,總的來說,通過封閉的國內電視世界挑戰克里姆林宮的宣傳在技術上似乎是不可能的。 這將需要在俄羅斯境內建立新的有線電視系統或廣播塔。 產生大規模替代信息運動的希望來自互聯網,並且偏向於更年輕的群體。 俄羅斯消息應用程序 Telegram 在群聊中有很多高調的批評,通常來自更強硬的支持戰爭的聲音。 這還不包括新聞網站和來自國外的 Youtube 廣播,最著名的是位於拉脫維亞里加的由俄羅斯流亡者經營的網站,瀏覽量達數百萬次。 因此,在某種程度上,該過程已經在進行中。 據現居美國的普京前高級顧問安德烈伊拉里亞諾夫說,“這需要時間。 在俄羅斯的俄羅斯人不會相信來自非俄羅斯人的任何消息或批評。 他們傾向於拒絕任何聽起來不愛國的東西。” 結果,像自由歐洲電台和英國廣播公司這樣的老牌媒體表現不佳,而裡加的媒體則表現更好。
俄羅斯流亡者組織有他們的問題,主要是因為試圖通過在反普京和親俄羅斯的同時制定中間路線來保持他們在俄羅斯國內的觀眾吸引力(波羅的海和烏克蘭人,以及許多其他人,不喜歡親-俄羅斯部分)。 一個突出的例子是 TV Rain(又名 Dozhd)最近不得不搬到荷蘭,因為它疏遠了當地的拉脫維亞人。 儘管如此,從廣義上講,利用克里姆林宮的新聞短缺的機會仍然存在,而且時機似乎是有利的。 如何利用它? 許多人建議在國外創辦一家俄羅斯移民媒體巨頭,包括娛樂和體育,在規模和魅力上可以與莫斯科的頻道競爭。 然而,如果克里姆林宮能夠在必要時有效地關閉部分互聯網,那麼誰會輕率地投入所需的大筆資金呢? 答案是衛星技術已經存在,足以繞過這些措施,Starlink 只是一個例子。 真正的問題在於內容:像 Illarianov 這樣的漸進主義者相信贏得民心是一場漫長的比賽。 但目前在烏克蘭發生的墮落屠殺可以說要求並非如此。
伊万娜·斯特拉德納 (Ivana Stradner) 等頑固的聲音呼籲採取更具攻擊性的直接宣傳策略:利用民族主義反對自己,煽動反對普京的極端親戰聲音,在法庭上煽動分裂,同時激起布里亞特人和喀山韃靼人等本已難以抗拒的少數民族反叛並脫離。 與俄羅斯同行相比,他們在烏克蘭動員和流失的人均比例更高。 (反徵兵抗議等阻力在這些地區更為強烈。)意想不到的結果可能是一場強硬的政變,領導層甚至更惡劣,但無論誰獲勝,都將忙於平息內部裂痕,也許是一場內戰,甚至可能導致俄羅斯聯邦解體。 這就是問題所在。 迄今為止,對於西方的大多數政策制定者來說,這是一個首先要避免的場景,因為它有可能導致大量難民湧入和核武器鬆動的噩夢。 但也許是時候制定應對此類不測事件的計劃了,所以爭論不休,或者看著烏克蘭人遭受數月或數年的毆打和屠殺,其他近鄰國家可能也會效仿。 正如斯特拉德納所說,“令人不安的場景可能遲早是不可避免的”。
來源:https://www.forbes.com/sites/melikkaylan/2023/02/02/the-west-is-failing-to-penetrate-the-russian-information-space-how-we-got-here-以及如何處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