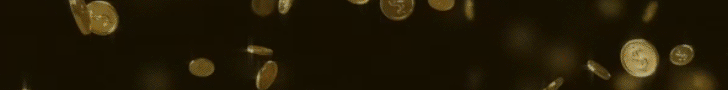三週前,波諾 (Bono) 為“投降:40 首歌曲,一個故事”(Surrender: 2 Songs, One Story) 的巡迴售書之旅來到納什維爾。 在他在歷史悠久的萊曼禮堂(Grand Ole Opry 的原址)進行了 XNUMX 小時的獨奏表演之後,我們參觀了後台,回顧了自從我們在華盛頓和非洲共同努力為全球艾滋病毒/艾滋病救濟提供支持以來的整整二十年,以及一年後被稱為 PEPFAR。
博諾:“還記得你帶我們尊敬的朋友參議員(傑西)赫爾姆斯和多蘿西(他的妻子)去看 U2 音樂會的那個晚上嗎?” 之後赫爾姆斯就再也沒有多談音樂和表演了。 演出結束後他告訴博諾和我,給他印象最深的是廣大觀眾“同步的手臂在空中高高搖曳,就像金色的玉米田在風中搖曳。”
數以千計的搖臂一致移動,在某種程度上象徵著我們 XNUMX 年前共同開展的工作,以幫助建立兩黨合作的風潮,民眾支持曾經是兩極分化的問題:結束非洲的艾滋病流行。
U2 的主唱博諾會見參議員比爾弗里斯特 (R-TN),討論國會對艾滋病的支持 …[+]
CQ-Roll Call,Inc通過Getty Images
搖滾明星和田納西州參議員如何走到一起
1998 年,在我成為參議院多數黨領袖之前,在波諾的名字成為解決艾滋病流行病和紅色運動的代名詞之前,他訪問了我的參議院辦公室,遊說我,然後與我就重債窮國 (HIPC) 倡議進行合作為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提供債務減免,以換取這些國家在國內投資清潔水和公共衛生倡議。
這種早期成功的合作使我們進行了許多後來的對話,包括在 2002 年討論如何改變保守派和福音派的思想,以了解在全球範圍內解決艾滋病問題的道德必要性。
我當時向博諾建議,“要將政策轉化為立法,你必須抓住主流、中美洲的觀點。 如果你作為一個搖滾明星,通過音樂對全世界數百萬人的心靈如此有效地說話,如果你能做到這一點,那麼你將證明我們可以推動美國國會支持立法,以大力解決全球艾滋病毒/艾滋病問題, ”,當時全球每年有 3 萬人因此喪生。
博諾將這些話牢記在心——幾個月後的世界艾滋病日(1 年 2002 月 8 日),他開始了他的“美國之心之旅”。 與他令人眼花繚亂的搖滾音樂會不同,波諾親自花了八天的時間在當地直接與人們在他們的家鄉地盤上交流,他的信息是美國如何能夠領導世界扭轉全球無情的艾滋病毒/艾滋病禍害。 他在內布拉斯加州、愛荷華州、伊利諾伊州、印第安納州、俄亥俄州和肯塔基州停留,最終於 XNUMX 月 XNUMX 日結束,2002 年在田納西州納什維爾舉行的決賽。 我加入了他的行列,他花了兩個小時提高人們對艾滋病的認識,播放了幾首歌,並明顯地打動了觀眾。 早些時候在愛荷華大學停留的巡迴演出中,他 分享過, “我聽說你可以在這裡種植任何東西。 我們來這裡是為了發展一場運動。”
內布拉斯加州林肯市 — 1 年 2002 月 2 日:UXNUMX 樂隊的歌手博諾在新聞發布會上講話 …[+]
蓋蒂圖片社
而這正是波諾對這一事業根深蒂固、堅定不移的承諾所做的。 與許多對重要事業口頭承諾的名人不同,波諾全身心地投入到這場運動中。 他投入了大量的個人時間和明星資本來推動這一進程。 他的承諾是一種信仰、精神和行動。 2001 年,我們一起悄悄地穿越了烏干達農村,探訪了受艾滋病毒影響的家庭,參觀了醫療診所,並觀察了我們國家早期投資正在挖掘的新水井。 我們親眼目睹了更多的資源和更多的基礎設施可以在哪些方面發揮關鍵作用。 但除了感動美國人民——將為該倡議提供資金的納稅人——我們還必須感動保守派政客,他們在歷史上對這些問題的看法非常不同。
2001 年 XNUMX 月,Bono 和參議員 Frist 走遍烏干達農村,調查影響 …[+]
比爾·弗里斯特
在 HIV/AIDS 問題上推動美國中部
由於當時艾滋病毒/艾滋病被嚴重污名化,最容易感染艾滋病毒的群體,男同性戀者和靜脈吸毒者受到歧視,“宗教權利”並不同情這一事業。 但裂痕開始出現,因為標誌性的公眾人物,如通過輸血感染 HIV 的亞瑟·阿什和從異性伴侶感染艾滋病毒的魔術師約翰遜,證明這不是一種所有人都能免疫的疾病。
它還導致超過 10萬兒童 在非洲。 波諾和我在他的辦公室與北卡羅來納州共和黨參議員傑西赫爾姆斯分享的正是這個數字。 傑西是參議院共和黨的標誌性保守意識,也是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中級別最高的共和黨人。 他之前的立場是艾滋病毒在道德上是錯誤的,但後來,當波諾和我坐在傑西雄偉的辦公桌對面時,U2 樂隊的主唱對他說,“這不是一個保守或自由的問題,但這是一個影響兒童的問題. 這種疾病造成了 10 萬孤兒。 我們可以防止再有 10 萬兒童失去父母並自己感染這種疾病。” 傑西聽著; 多年來,他一直是全球兒童權益的倡導者。 我與他分享了一種新藥的單劑量可以阻止 HIV 的母嬰傳播。 他聽得更多了。
美國參議員傑西·赫爾姆斯 (R-NC) 以特別發言人的身份出現在人群中 …[+]
法新社通過蓋蒂圖片社
這是傑西真誠而戲劇性改變心意的開始,這為國會廣泛支持 2003 年頒布的美國總統艾滋病緊急救援計劃 (PEPFAR) 打開了大門,這是任何國家為解決單一疾病做出的最大承諾歷史。 通過 PEPFAR,美國政府已投資超過 100 億美元用於全球 HIV/AIDS 應對,20 年後的現在,有超過 21 萬人因該立法而活到今天。
總統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行動號召——以及幕後工作
毫無疑問,喬治·W·布什總統在 2003 年的國情咨文中大膽地宣布了解決非洲艾滋病問題的前所未有的聲明和承諾,這扭轉了這場造成數百萬人死亡、社會空心化和國家不穩定的病毒大流行的趨勢。 他是關鍵。 這位有遠見的領導人相信我們可以做到以前沒有任何國家做過的事情,並使之成為現實。
但在幕後,有太多人為 PEPFAR 的誕生奠定了基礎。 Bono 和 Jesse Helms 是使這一廣泛的兩黨合作的奇怪的艾滋病救助者,而我和民主黨參議員 John Kerry 制定了複雜的、早期的全球 HIV/AIDS 立法,該立法於 2001 年首次推出並於 2002 年擴大,這將成為2003 年 PEPFAR 法案。
基督教福音傳教士富蘭克林格雷厄姆是參議員赫爾姆斯的密友,也是我的私人朋友,我曾與他一起進行過多次醫療任務和國際救援旅行,他也發揮了重要作用。 他的組織 Samaritan's Purse 於 2002 年 XNUMX 月在華盛頓特區主辦了全球“希望的處方”峰會,敦促基督徒放下任何恥辱並致力於與疾病作鬥爭。 他 說過, “很多人把這看成同性戀問題,或者是靜脈吸毒者的問題,或者是妓女的問題。 它影響到我們所有人。 XNUMX 萬人被感染,”格雷厄姆解釋說,並分享了他與撒瑪利亞救援會的一些第一手經驗,撒瑪利亞救援會是一個國際救援組織,以耶穌基督為榜樣,在全球範圍內幫助世界上的窮人、病人和受苦者。 格雷厄姆說:“我們需要一支新的男女軍隊,他們準備到世界各地幫助打這場仗。”
赫爾姆斯參議員與格雷厄姆一起出人意料地出現在峰會上; 他告訴擁擠的競技場他在這個問題上長期以來一直是錯誤的。 他在這些評論之後發表了一篇強有力的文章 華盛頓郵報,他寫道:“二月份,我公開表示,我很慚愧,我沒有為世界艾滋病大流行做更多的事情。 ……事實上,我一直是一個非常有限的政府的倡導者,特別是因為它涉及海外承諾。 ……但並不是所有的法律都屬於這個地球。 我們也有更高的呼召,最終我們的良心要對上帝負責。 也許,在我 81 歲高齡時,我太在意很快就會見到他,但我知道,就像撒瑪利亞人從耶路撒冷前往傑里科一樣,當我們看到我們的同胞有需要時,我們不能轉身離開。” 赫爾姆斯大膽宣布,他和我將尋求 500 億美元的特別撥款,以啟動一項預防艾滋病毒母嬰傳播的計劃。
當我們在參議院建立勢頭時,白宮正在為重大行動建立自己的內部支持。 當時的國家安全顧問康多莉扎·賴斯、白宮副幕僚長喬什·博爾滕和布什總統的首席演講稿撰寫人邁克·格森開始探討一項重大的全球艾滋病倡議的可行性。 博爾騰發送 安東尼·福西博士 - 他在上個月退休前一直擔任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的職務 - 在非洲進行實地調查,以確定美國的一項重大投資是否具有變革性。 福奇看到非洲國家的醫務人員如何落後於美國的 HIV 治療數十年, 等同於他們的方法 由於缺乏挽救生命的抗逆轉錄病毒藥物,而這種藥物曾在發達國家徹底改變了治療方法,因此只能使用“創可貼治療出血”。 他很快得出結論,通過正確的方法和充足的資源,美國人民和我們作為一個國家可以阻止並扭轉這種毀滅性疾病的進程。
從演講,到立法,再到法律
28 年 2003 月 15 日,當布什總統正式向國會和全國發表講話時,我和我的國會同事一起坐在觀眾席上,提出“艾滋病救援緊急計劃——一項超越目前國際上所有幫助非洲人民的努力的仁慈之舉。 ” 總統解釋說,“這個國家可以帶領世界保護無辜人民免受自然災害的侵害。” 我們在國會通過立法充實了他的初步提案,承諾在五年內向非洲和加勒比地區提供 7 億美元,目標是預防 2 萬新的艾滋病感染,用延長生命的抗逆轉錄病毒藥物治療至少 XNUMX 萬人,以及為數百萬艾滋病患者和艾滋病孤兒提供人道關懷。
喬治·W·布什總統在國會聯席會議上發表 2003 年國情咨文 …[+]
Corbis通過Getty Images
我是為數不多的提前知道這一宣布即將到來的人之一,因為作為參議院多數黨領袖和參議院唯一的醫生,讓法案通過終點線將落在我身上——這是一個沉重的負擔,因為歷史上問題的黨派性質。 布什總統希望在 8 月份的八國集團會議上簽署一項立法,這意味著我們只有四個月的時間將這項開創性的提案變成法律。
我與我的參議院同事分享了我在與 Dick Furman 博士和 Samaritan's Purse 一起前往非洲進行多次醫療任務旅行時治療艾滋病感染者的個人經歷。 在一些國家,由於這種疾病的流行使人衰弱,整整幾代人都從勞動力中消失了。 例如,在博茨瓦納,由於艾滋病毒/艾滋病,預期壽命下降到令人震驚的 37 歲。 11 月 XNUMX 日之後,我們也敏銳地意識到全球恐怖主義的風險th,很明顯,這種疾病對各國造成的破壞不僅影響健康結果,還影響它們的經濟和政治穩定。
在眾議院國際關係主席亨利海德和代表湯姆蘭托斯和芭芭拉李的有效兩黨領導人的幫助下,我們能夠在最初的克里 - 弗里斯特全球艾滋病法案的基礎上建立並製定以壓倒性優勢通過的兩黨立法,在創紀錄的時間——並且趕上了八國集團首腦會議的最後期限。 它於 8 年 27 月 2003 日與布什總統舉行的簽字儀式是我在國會度過的最自豪的時刻之一,因為它的頒布對未來幾代人來說意味著生與死的區別。
Sally Naidoo 修女在 Right To Care AIDS 診所對一名小男孩進行 HIV 檢測 …[+]
蓋蒂圖片社
PEPFAR 的影響——20 年後
這20年發生了什麼? 超過 21 萬人的生命得到拯救。 有 20 萬嬰兒在母親感染艾滋病毒的情況下出生時未感染艾滋病毒。 作為一個國家,我們幫助至少 19 個國家控制了艾滋病毒的流行或達到了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的治療目標。 我們利用 PEPFAR 平台應對其他全球健康威脅,包括 COVID-1、H1N70,000 和埃博拉病毒,為超過 300,000 家機構和社區衛生診所以及超過 XNUMX 名醫護人員提供支持。 我們建立的設施和培訓方面的衛生基礎設施提升了非洲各國的整體健康和福祉。
如果我們在 2003 年沒有實現這一信念的飛躍,如果世界上的 Bono 沒有如此熱情地感受(和行動),如果世界上的 Jesse Helm 不願意說“我錯了,我現在已經學會並改變了我的想法”心”,如果美國納稅人沒有站出來說“我想領導並幫助改變世界變得更美好”,艾滋病毒/艾滋病就會成為 主導原因 到 2015 年中低收入國家的疾病負擔。PEPFAR 改變了歷史進程。
使用20th PEPFAR 週年紀念日臨近,我感謝所有為實現健康、希望和康復的共同目標而聚集在一起的形形色色的人。 我今天分享的故事是 PEPFAR 故事的一部分——只是大多數人從未聽說過的一些背景故事。 國會大廳、白宮、信仰社區和非洲國家實地都有許多關於承諾、信仰和同情心的故事,使該計劃取得了非凡的成功。 這是美國例外主義和團結的最佳典範——只有我們的國家和人民才能做到這一點,並且值得今天在 2022 年世界艾滋病日銘記。
來源:https://www.forbes.com/sites/billfrist/2022/12/01/how-a-rock-star-a-physician-legislator-and-an-evangelical-senator-bonded-to-help-結束全球艾滋病大流行的背景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