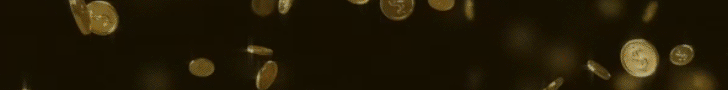Halestorm 的 Lzzy Hale 將於 2022 年 XNUMX 月演出
蓋蒂圖片社
很容易假設關於心理健康的對話在硬搖滾和金屬界是不受限制的。 Lzzy Hale,格萊美獲獎樂隊的主唱 駭兒史東樂團,說再想一想。
“我已經看到了它的兩面。 一方面,這個社區實際上是受壓迫者的聖地。 金屬和硬搖滾音樂一直是與眾不同的人、不適應的人、有精神問題的人的擁護者。 這是我們可以談論這些事情的類型,”她說。
“與此同時,這就像一個硬漢生意,社區中的某些成員會說,‘我永遠不會見到治療師,因為那意味著我真的瘋了’之類的。 但這也開始以非常快的速度消失。 我喜歡這樣一個事實,現在我們更多地談論打破這種污名。”
硬朗是污名開始瓦解的原因之一。 在金屬樂隊 Huntress 的 Jill Janus 於 2018 年自殺身亡後,黑爾寫了一封她在 Instagram 上分享的信,敦促社區更公開地談論心理健康,承認她自己的“黑暗迷宮”並向苦苦掙扎的粉絲保證他們並不孤單. “尋求幫助並不意味著你已經崩潰了,”她寫道。
“這或多或少是我創造一個例子,讓我們每個人都不孤單,看看有多少人,僅僅通過舉手——或者就像我說的,‘舉起你的角,拍張照片’——會回應的,”她說。
“而且這個數字很淫穢,有多少人說,‘謝謝。’ 這幾乎就像我允許他們談論它一樣。 每個人的生活中都會有一個轉折點,無論他們的職位如何,當他們剛剛受夠了面紗時,通過分享我自己的旅程以及我應對抑鬱、焦慮或驚恐發作的方式,我得到瞭如此多的愛因為我認為大多數人都需要聽到其他人正在經歷它——尤其是在我這個位置上的人,看起來一切都很好,而且一直都很花哨。”
雖然這一刻對黑爾來說很重要,但這並不是她第一次解決心理健康問題。 這些談話可以追溯到中學,大約在她與弟弟 Arejay 組建最終成為 Halestorm 的時候。
“在我們組建樂隊之前,我會在學校驚恐發作。 當我什至不知道那是什麼時,我有強烈的焦慮和抑鬱。 我正在經歷這些我不一定知道如何擺脫的感覺的浪潮,我認為音樂給了我那個我可以稱之為我的世界的角落,幫助我擁有我是誰,擁有我的怪異,是什麼讓我我與眾不同,”黑爾說。 “我開始和我的同齡人談論這件事,告訴他們你需要找到屬於你的東西。”
隨後多年的狂熱和好評為黑爾提供了一個談論心理健康的平台,她欣然接受了這個機會。 “你不一定決定開始做這些事情,你只是被感動為某些事情挺身而出。 我很自豪能處於我能做到的位置,”她說。
但是當大流行來襲時,她發現自己又回到了一個非常脆弱的地方——Halestorm 的最新專輯就是從這個地方, 死而復生, 出生於。
“突然間,我面臨著,‘哦,我不再是搖滾明星 Lzzy Hale。 我是伊麗莎白·黑爾,穿著睡衣坐在沙發上,有著不可預見的未來,”她說。 “所以我不得不把它寫下來。 我覺得我與不同類型的真理聯繫在一起。 對我來說,把這些東西拿出來很重要,寫很多這樣的歌曲幾乎是對自己的鼓舞,並嘗試預測未來,因為沒有真正的計劃。 我們要進工作室嗎? 我們要出唱片嗎? 我們還會再去巡演嗎? 就在這一刻,我能做什麼? 我會寫作,這是多年來我第一次不為任何人寫作,除了我自己。”
“我哭了好幾次,因為我覺得我需要把它弄出來,”黑爾補充道。 “這張專輯有很多黑暗之處,但對我來說,始終找到那束光、那份希望並堅持下去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如果我只是讓自己盤旋而出,深入那條黑暗的道路,我不知道我是否會在另一邊成功。 這讓我很困惑。 我有點身份危機,尋找目標,幾乎不得不提醒自己我到底是誰。 你沒有意識到你不僅在舞台上使用了你的角色,還使用了你與樂隊成員的友情,巡迴演出和專輯發行的進步,更不用說現場表演只是首選的藥物。 沒有這些東西,它會慢慢消失,你必須找到新的方法。”
現在這張專輯自 XNUMX 月以來一直在野外,而 Halestorm 又重新開始巡迴演出,她正在享受與社區更深層次的聯繫。
“我從這個核心事實中意識到,在這些感受中,我從來都不是一個人。 我正在觀看這些時刻與正在聽這些歌曲的人實時發生,現在它不再是我的歌,而是他們的歌。 這些人的手臂上紋著線條,我收到人們的來信,說這條線條或這首歌改變了他們的生活,”她說。
“這是一個如此美好的時刻,當你擁有這些對你來說非常個人化的歌曲時,你必須創作這些歌曲才能度過難關,然後突然之間,你將這些信息傳遞給那些可能沒有工具或對自己說這些事情的能力。 他們現在可以擁有它——這就是它的全部意義所在。”
資料來源:https://www.forbes.com/sites/cathyolson/2022/11/04/mind-reading-halestorms-lzzy-hale-is-hell-bent-on-busting-the-mental-health-stigma-硬搖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