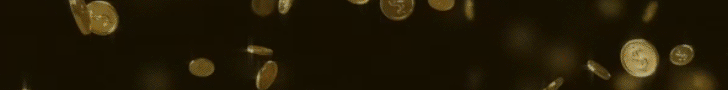洛杉磯新奧爾良 – 04 月 2014 日:約翰·福格蒂 (John Fogerty) 在 XNUMX 年新奧爾良爵士樂與傳統音樂節期間表演 …[+]
WireImage
在唱片音樂史上,很少有藝術家與唱片公司之間的爭鬥像 Creedence Clearwater Revival 聯合創始人歌手、詞曲作者兼吉他手 John Fogerty 與 Fantasy Records 之間的爭鬥一樣激烈。
在 1968 年發行同名首張專輯後,CCR 繼續在全球銷售超過 50 萬張專輯。 Fantasy 所有者 Saul Zaentz 在 70 年代進一步開始了電影製片人的職業生涯,並獲得了三項奧斯卡最佳影片獎。
1980 年,Fogerty 將他的 CCR 版稅交給了 Zaentz,以試圖退出他與唱片公司的唱片合同。 隨後兩人之間的訴訟歷史是 充分證明1985 年,廠牌高管臭名昭著地起訴 Fogerty 剽竊自己,一場反訴最終由美國最高法院以 Fogerty 勝訴而告終。
雖然 Fogerty 保留了他個人作品的所有權,但他曾多次試圖收回他為 CCR 創作的歌曲,最終在 1989 年與 Zaentz 親自會面後,最終放棄了這不可能發生的命運。
這位詞曲作者和吉他手慢慢開始與他的 CCR 歌曲和平相處,1987 年首次在退伍軍人面前表演這些歌曲,同時在密西西比州的一次意外相遇後繼續將它們放回到他的現場演出中,探索 神秘與民間傳說 1990 年十字路口周圍的藍調歌手羅伯特·約翰遜 (Robert Johnson)。
休斯敦——11 月 XNUMX 日:(LR) 美國鼓手道格克利福德和美國音樂家、歌手和小學 …[+]
蓋蒂圖片社
Zaentz 於 2014 年去世,最終在 2000 年代初期將 Fantasy Records 出售給 Concord Music Group。 從那裡開始,Concord 在出售後恢復了該集團的版稅,Fogerty 為他近 25 年來首次創作的 CCR 歌曲支付了版稅。
雖然他已經學會了接受他可能永遠無法重新獲得歌曲所有權的想法,但他的妻子朱莉還是敦促福格蒂再試一次,她最近與康科德進行了對話,這導致了他的 重獲多數股權 在 CCR 的全球出版中,涵蓋了跨越五個多世紀的一系列事件。
“嗯,很明顯並且可以理解,我不想把我的全部信仰或精力投入其中。 你已經非常失望了,”福格蒂解釋道。 “我會告訴朱莉,‘嗯,你知道的,親愛的,太棒了。 感謝您投入精力。 但我沒有屏住呼吸,這是肯定的,”他說。 “我認為我最大的感受是如釋重負——因為我已經為此苦苦掙扎了很長時間。 簡單來說,我一直覺得我的歌沒有自己的所有權是不對的。”
我跟 約翰·福格蒂 關於奪回他的 CCR 歌曲的戰鬥,在策劃他的音樂的商業佈局、美國版權法以及與兒子泰勒和肖恩在舞台上表演方面有了新的幫助。 下面是我們電話交談的文字記錄,為了篇幅和清晰度而進行了輕微編輯。
吉姆瑞恩:我們處在一個每個人都在出售目錄的時代——你設法買了你的目錄。 現在有一些時間來反思,這些歌曲的回歸對你來說意味著什麼?
約翰·福格蒂: 當然有很多不同的情緒。 我認為我最大的感受是如釋重負——因為我已經為此苦苦掙扎了很長時間。 簡單來說,我一直覺得我的歌沒有自己的所有權是不對的。
很久很久以前,當我第一次意識到情況就是這樣的時候,我想我感到很震驚。 似乎總是錯的。 當你有點無助時,你只是在掙扎。 各種感覺交織在一起——感到無助。 你也有點生氣,因為另一方——擁有你歌曲的人——正在與他們共度美好時光,賺了很多錢,並決定何時何地放置你的歌曲或使用你的歌曲。 所有這些過去真的很困擾我。
我想現在我只是感到寬慰,因為我不必繼續為之掙扎。
John Fogerty(左)和 Kenny Aronoff(右)在 Bourbon and Beyond 音樂節的舞台上表演。 …[+]
攝影:Barry Brecheisen
瑞安:我讀到過關於您在 1989 年接近獲得版權的消息。您與 Saul Zaentz 和 Bill Graham 進行了面對面的會談。 那顯然是南下了。 在最近一輪談判之前,您最後一次真正實質性地接近了收回歌曲的想法嗎?
福格蒂: 以一致的方式。 那是最後一次。 聽起來你一定讀過我的書。
這兩次會議的後果持續了多年。 我會說,我被束縛在一種傲慢的方式中。 就像貓捉老鼠一樣。 我一直相信,一直相信,一直相信——可能直到 1994 年,甚至更晚。
有一次,當我在慢跑時,我終於聽到了不可避免的聲音——這不會發生。 我終於倒在地上,意識到我沒有希望了。
所以,那一刻,我鬆了一口氣。 因為我放棄了掙扎。
瑞安: 之後 30 年過去了。 你學會接受那個現實。 30 年後,朱莉建議再試一次。 你對這個想法的最初反應是什麼?
福格蒂: 嗯,很明顯並且可以理解,我不想將我的全部信念或精力投入其中。 你已經深深地失望了。 我怎麼說呢? 如果你遇到的事情真的很痛苦和消極,你就會厭惡——你不想再去那裡了。 而且您還以一種宿命論的方式看待它。
我會告訴朱莉,“嗯,你知道的,親愛的,太好了。 感謝您投入精力。 但我沒有屏住呼吸,這是肯定的。”
洛杉磯新奧爾良 – 04 月 2014 日:約翰·福格蒂 (John Fogerty) 在 XNUMX 年新奧爾良爵士樂與傳統音樂節期間表演 …[+]
WireImage
瑞安:我讀到 Concord 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建立您的版稅。 即使那是近 20 年前的事了。 但是,就這種關係而言,這種情況是否開始緩和水面或改變一些事情?
福格蒂:那大約是 2005 年。重新建立聯繫似乎是個好主意。 因為他們對 Norman Lear 有了新的所有權。 而且,當然,他的整個形象,至少在電視上是這樣,他似乎是一個相當開放的人,可能像我一樣偏左。 那就是那件事發生的時候。 這就是氣氛。
非常棒的是,他們恢復了我自 1980 年以來一直丟失和拒絕向我支付的藝術家版稅。所以那是 25 年我沒有支付藝術家版稅的時間。 最終,這方面有所增加。 所以我有點接近他們了一段時間。
但是……我想我會以商業方式說唱片公司是公司——他們是企業。 他們最終會像企業一樣行事。
我看得出來,雖然我們曾討論過我或許可以在某個時候購買我的版權的想法,但當時我在經濟上無法做到。 我有點祈禱並打開了這個主題,希望我們能找出某種財務現收現付的想法或類似的東西。 它從來沒有真正具體化。 因為他們顯然並不急於這樣做——至少可以這麼說。
當然,他們擁有 Creedence 的主人,並且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又回到了某種程度上做任何事情——把歌曲放在他們想放的地方。 大多數時候,我什至沒有聽說它什麼時候會發生。 在過去的幾年裡,他們實際上已經給我或朱莉發了通知,通知我們有事情要發生。
最終,感覺就像以前一樣。 所以,我沒有太投入。 當感覺大聲喧嘩有點無用時,你就會停止大聲喧嘩。
John Fogerty(右)和兒子 Shane Fogerty(左)在 Bourbon and Beyond 的舞台上表演 …[+]
攝影:Barry Brecheisen
瑞安: 看過這個故事 鮑勃迪倫有點刺激 你在 1987 年表演“驕傲的瑪麗”。從那時起,你開始重溫 CCR 的一些現場表演,首先是在退伍軍人面前表演。 當你這麼長時間以來第一次踏上那條路,重新審視那些材料時,最初的感覺是什麼?
福格蒂: 起初,在 1987 年,我知道,儘管我做了一些我默認的事情,但我仍然有一種心理和心理上的立場,即我沒有做那些歌。 我對 Fantasy 和 Saul Zaentz 對待我的方式感到非常強烈。 這是個人的。 因為,一開始,在 Creedence,我真的是這個標籤上唯一的藝術家。 他是唯一的僱員。 所以基本上是一對一的。 當事情變得更大時——我想主要是通過我的努力——你覺得對他們的成功負有很大的責任。 因此,被排除在分享成功之外是一顆難以下嚥的苦藥。
我改變主意的那一天實際上是站在羅伯特約翰遜的墳墓前。 那是一個真實的故事。 我真的不知道那會以那種方式發生。 我沒有找到那個。 我只是一個音樂愛好者和一個藍調愛好者——一個神秘愛好者——在 1990 年曾幾次去密西西比州尋找這個偉大的謎團。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如此被迫。
所以我站在羅伯特的墓前。 我很難進去摸那棵我認為他被埋在下面的樹。 因為沒有標記或任何東西——這都是民間傳說。 然後拖著自己穿過荊棘叢和其他地方大概花了半個小時左右。 地面上還有大約三四英寸深的水,所以我有點像釣魚探險。
但我有時間思考我剛剛做了什麼。 在密西西比州炎熱的陽光下,我想知道羅伯特的歌曲發生了什麼事,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他的歌曲歸功於誰或歸誰所有。 我的[心理]畫面是某個律師在一座高大的城市建築裡抽著雪茄,放著羅伯特的歌曲,這讓我很反感。 我在心裡說:“沒關係,羅伯特! 每個人都知道那是你的歌! 我們都知道它們是你的。” 當我說出這句話的那一刻,我就意識到,“好吧,約翰,你處於同樣的位置。 在你像羅伯特約翰遜那樣躺在地上之前,你需要先播放你的歌曲。” 它變得非常清楚。
它讓我擺脫了我為自己建立的這種非常強烈的心態。 這是一個棘手的結——我不知道如何解開它。 而這種解開它。 非常引人注目的是,我又開始將自己與自己的歌曲聯繫起來。
John Fogerty 在 Telluride Blues and Brews 音樂節上登台表演。 13 年 2019 月 XNUMX 日,星期五 …[+]
攝影:Barry Brecheisen
瑞安: 你很早就開始關注這個了。 但是從油漆稀釋劑廣告之類的東西到,比如說, 阿甘, 多年來,您的音樂有一些用途,有些很有品位,有些似乎……不太有品位。 你幾乎無法控制其中的任何一個。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這都是一種詛咒,但現在看到音樂在商業上的使用真的很普遍。 現在您實際上已經參與了該過程,您希望如何策劃它向前發展?
福格蒂:(笑)自從邁克爾·傑克遜以及互聯網以來,油漆稀釋劑廣告就變得令人嚮往!
你知道,我是 60 年代的孩子,那時候,讓你的音樂在電視上被任何公司使用的想法——尤其是香煙、酒精……凝固汽油彈——是非常噁心的。 你只是假設你的觀眾會來看你的節目並向你扔爛番茄。 那隻是一種嬉皮心態——我也完全歸因於此。
我記得看到 Bob Hope 為一家銀行做廣告。 你只是看了看然後說,“他的錢還不夠多嗎? 他為什麼要那樣做? 這看起來很便宜。” 這就是孩子們對這些事情的感受。
其中一個重大變化——我一直聽到年輕樂隊這樣說——是“好吧,我們無法在其他任何地方播放我們的音樂。 那麼,如果他們想在電視上播放廣告呢? 偉大的。” 現在有一些道理。 尤其是像我這樣的人,真的很難在任何地方播放一首新歌。
所以,我當然對整件事持更開放的態度——尤其是,一部好電影會很棒。 但是,是的,這些年來有很多我認為他們可以拒絕的臭電影,你知道嗎?
瑞安: 他們從不拒絕。 (笑)
福格蒂: 嗯,原來如此! 你打了它的頭。 他們拒絕的價格永遠不夠便宜。 我總是說這樣的話,“他們正在彎腰撿起一角錢。”
瑞安:我通過“幸運之子”對 CCR 的介紹是 阿甘. 我當時 14 歲。然後我爸爸填補了空白。 現在擁有全球發行權,並且能夠更直接地審查、指導和策劃這一過程,你認為它是一種可以用來確保你的音樂以有意義、有品位的方式接觸到新一代年輕一代的工具嗎?
福格蒂: 我想是這樣。 這可能是最好的描述——授權你的音樂,試圖讓它可見並讓它出現在一些地方。
您過去常常嘗試讓您的音樂出現在年輕人面前,一個聽自己類型或流派音樂的孩子。 我的道路可能會像電影配樂一樣在不尋常的情況下與他交叉。 它甚至可能必須是 Netflix 或 Hulu 等流媒體平台上的商業廣告。 我一直聽說年輕人甚至不再看有線電視了。
瑞安:Creedence Clearwater Revival 最初是一個家庭樂隊。 現在,每個晚上在舞台上,您都可以再次以這種方式慶祝您的音樂,與您的兒子們一起表演。 你再次擁有這些歌曲。 看到和體驗一切都像那樣圓滿是什麼感覺?
洛杉磯新奧爾良 – 04 月 2014 日:約翰·福格蒂 (John Fogerty) 在 XNUMX 年新奧爾良爵士樂與傳統音樂節期間表演 …[+]
WireImage
福格蒂:好吧,諷刺的是我並沒有失去。 我和我哥哥有一個樂隊。 而且,在早期,它是如此美好——如此友好,如此快樂地實現你的目標,你的夢想似乎如此遙遠。
如今,站在舞台上演奏這些非常美妙的歌曲,讓我感覺非常好,與家人分享——事實上我的兩個兒子是兄弟,處境和我一樣——這是我最快樂的境遇”我曾經有過音樂。 因為未來似乎是無限的,不會減弱的。
這真的很快樂。 每天晚上 [在舞台上],我都會和兒子 Shane 進行吉他對決。 能夠以如此積極和快樂的方式體驗音樂真是太棒了。
瑞安: 好吧,這場戰鬥已經打了 50 年,您對美國版權法的陳舊理念有何了解?當年輕音樂家開始審視或完全無視合同時,您會給他們提供什麼樣的建議?
福格蒂: 天啊……好吧,我對美國的版權法很憤世嫉俗。 我很憤世嫉俗。 特別是音樂出版。
整件事似乎非常不利於任何類型的年輕且無知的作家,他走到這樣的境地,一方面,他有點迫切希望被邀請分享他創作的任何東西。 事實被隱藏了。 這位年輕作家的想法是,“嗯……我們可能會給你一個機會,但是,當然,我們將不得不讓你簽署這個……”有 200 年的聰明人欺騙有創造力的人。 或者更長。 那是關於的故事 該歌劇魅影. 這是一回事。
所以,我的建議,尤其是對年輕的詞曲作者來說,你是否有權擁有你的歌曲——出版你自己的歌曲。 不要讓他們欺騙你。 他們會試圖用你要開始錄音和所有這些東西的想法來給你壓力——但你總是會後悔的。 它會持續你的餘生——就像我一樣。
在某些時候,你真的會決定放棄它,或者像我一樣讓他們從你身邊被騙——這不值得。
Source: https://www.forbes.com/sites/jimryan1/2023/02/27/john-fogerty-on-50-year-battle-to-recapture-the-music-of-creedence-clearwater-revival/